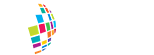【www.ym16.com - 移民政策】
C. 区域性倡议
由于对经济一体化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政治一体化的推动,出现了若干有时也触及工人流动内容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在这方面,欧洲联盟是走在最前列的区域集团。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条约纳入了成员国工人自由流动的条款。1993年,欧盟实现了全体公民在其成员国境内的自由流动。然而,在10个新成员国于2004年5月加入联盟时,在2011年截止的过渡期内,对这些国家的公民在联盟内的流动施加了限制。除了规范成员国公民在欧盟境内的自由流动外,欧盟还与原籍国建立伙伴关系;拟定了共同的欧洲庇护政策;促进公正对待在欧盟成员国居住的第三国国民。
在其他区域,促进人员流动或工人流动的协定已成为建立共同市场或自由贸易集团的规范框架下的组成部分,但进展情况都不如欧洲联盟。例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中非经货共同体)关于人员自由流动的议定书尚未得到执行。在亚洲,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设立了商务旅行卡,以便利商务旅行和商业流通。在美洲,南方共同市场已通过各种文书,促进缔约国之间的游客和商务旅行者的流动,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则载有向其缔约国熟练工人发放特别签证的规定。
1995年以来大量出现的非正式协商进程,是一种新型区域合作。最先出现的进程之一,就是1985年为商讨庇护问题设立的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庇护、难民和移徙政策政府间协商。发展中国家之间设立的第一个区域进程包括中美和北美洲国家,是1996年在墨西哥普埃布拉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起的。根据联合国和移徙组织的统计,如今在美洲有2个区域进程,亚洲有3个,非洲有2个。欧洲至少有4个区域进程(United Nations,2005a;IOM,2003)。这些进程具有的非正式特性,促进了对话和信息交流。这些进程把原籍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以及不同政府部门的代表汇集一堂,促进了国际以及国内的协调一致。对这些进程的影响力进行评估为时尚早,但它们看来在建立共识、推动合作以及促进能力建设方面有所建树。
延伸阅读
国际移徙与发展:就国际移徙展开政府合作(4)
D. 双边做法
采用双边协定以把移徙合作安排正规化。这些协定旨在确保移民流动在有关国家互惠的情况下进行。根据劳工组织开展的各国政府调查,提出报告的66个国家缔结了595份双边协定。在报告的协定中,10个国家占一半左右。协定数量在不断增加:按年平均计算,2000年到2003年缔结了29份协定,1990年到1999年缔结了19份,1980年到1989年缔结了11份。大多数协定(63%)涉及欧洲国家,11%涉及加拿大和美国,60%是1990年后缔结的。
双边协定涉及各种问题:其中57%纳入了关于协调社会保障应享权利和付款的条款;18%涉及外来工人计划或一般性劳工迁移交流;12%涉及受训人员或年轻专业人员的入境;5%涉及季节性移民。
劳工组织的调查范围远远不够完整。Mármora(2003)认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在1991和2000年之间缔结了84份双边协定,半数以上是同其他区域国家缔结的,比劳工组织报告的数字高一倍以上。由于双边协定没有集中登记册,其数目仍然难以确定。此外,考虑缔结此类协定的国家没有判定最佳做法的直截了当的办法。设立便于查阅的双边协定保存体系,将是有益的。
向劳工组织报告的再入境协定非常少见。它们与原籍国或中转国允许身份不正常的移徙者再入境有关。根据上述政府间协商的资料,截至2000年5月,已达成320份再入境协定或安排,其中302份是1990年以后达成的。再入境协定也是欧洲联盟减少非正常移民战略的组成部分。这些协定中包括欧盟和合作伙伴国家为就非正常移民的回返展开合作而作出的对等承诺。到2005年,欧洲联盟委员会与11个国家开展协定谈判,但到2006年5月为止,仅缔结了其中4项协定。
一些国家利用双边协定来推动安全、及时的汇款活动。加拿大与一些加勒比国家签署协定,允许将工人收入的一部分自动移交给本国的家人(Ruddick,2004)。2003年,菲律宾和美国互换加强汇款渠道问题谅解备忘录,以促进信用社参与汇款业务(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Government of the Philippines,2004)。
双边做法给各国政府带来了相当大的灵活性,这是因为可以根据相关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每项协定的规定。但不应利用这些协定来规避或绕过国际条约或习惯法规定的义务,例如关于难民的义务。此外,在移徙管理方面,对规定不同的许多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追踪,增加了行政负担。或许有必要建立国家机制,确保双边协定的执行工作,并促进宣传和了解已生效双边协定的规定。
国际移徙与发展:就国际移徙展开政府合作(1)
A. 规范性框架
大会通过的人权文书以及国际劳工会议通过的关于移徙工人的文书,构成了国际移徙问题国际规范性框架的核心(见表13)。1946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为人权保护体系奠定了基础。《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1990年)是移徙工人权利方面最全面的国际公约,已得到34个会员国的批准,是七项核心国际人权文书中最新的一项,这些文书共同构成了联合国人权条约体系。其他六项文书是:(a)《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b)《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c)《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d)《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e)《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f)《儿童权利公约》。在批准后,所有国家均受到七项核心人权条约中至少一项条约的约束。因此,这些文书为在一国境内保护每个人(无论公民还是非公民)提供了依据。这些文件载明的各项人权适用于所有人,其原因并不在于是否拥有公民地位,而是因为大家同属人类。
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也与移民权利的保护相干,其中规定外国国民有权同本国领事当局联系,而且在遭到逮捕或拘留时由接收国官员告知其这一权利。
在就业领域,劳工组织各项公约制定了适用于所有工人(包括移民在内)的国际公认的劳工标准。两项文书具体论及移民工人。劳工组织第97号公约于1949年通过,其中载有关于雇用正常情况下的外国移民工人时保证给予与本国国民相同的平等待遇。该公约得到45个国家的批准。劳工组织1975年第143号公约在第一部分中论述了非正常移民问题,并在第二部分中规定,正常情况下的移民工人不仅有权享有与国民相同的平等待遇,而且在就业、工会权利、文化权利以及个人和集体自由方面享有均等机会。已有19个国家批准该公约。
2005年,劳工组织召开的三方专家会议通过《劳工组织劳工移民问题多边框架》,为各国政府、工人组织以及雇主组织以注重权利的办法处理劳工移民问题提供了一整套不拘约束力的原则、准则和最佳做法。在促进所有人拥有体面工作这一广泛背景下,《框架》旨在推进劳工组织三大构成方之间的合作与磋商,协助切实执行关于劳工移民的政策。2006年,劳工组织理事会授权总干事推动劳工组织成员国在拟定劳工移民政策时采用《框架》的原则和准则。
上文G节讨论的两项国际文书侧重于防止和起诉人口贩运和偷运移民的犯罪。关于人口贩运的议定书已有97个缔约国,并于2003年生效。关于偷运移民的议定书已有89个缔约国,并于2004年生效。
有两项联合国文书论及难民保护。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了对“难民”一词的定义和难民的法律保护。该公约还禁止驱逐或强行遣返已获得难民地位的人。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将1951年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1951年1月1日后成为难民的人,而且没有作出任何地理限制。全体会员国中已有四分之三加入《公约》和《议定书》,使之成为最为广泛接受的难民问题文书。
除各项国际文书提供的规范性框架外,1990年以来举行的联合国会议和首脑会议达成的无约束力成果文件提供了行动框架,以最大程度地发挥移徙给发展带来的益处。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于2006年出版了《关于国际移徙和发展的建议简编》,以便于评估这个全面框架可在何种程度上指导政府间合作与对话,推动涉及移徙问题的共同发展倡议。
最后,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于1995年1月生效,其中载有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框架。该框架中与方式4有关的各节涉及自然人为出国提供服务进行的临时流动。今天,方式4约占服务贸易总额的1%。《总协定》未对“临时”一词作出界定,因此它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总协定》涵盖的商务访客通常可以居留多达3个月,而公司内部调派人员可以居留3至5年。在目前进行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正在努力将方式4进一步自由化,特别是在低技能工人流动方面。然而,迄今没有什么进展。
国际移徙与发展:打击人口贩运
贩运和偷运是置受害人的性命于危险境地的犯罪行为。打击和防止这些犯罪行为的工作若要奏效,就必须明确认识贩运和偷运之间的区别。依照《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第3条a款,人口贩运系指“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剥削应至少包括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
《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徙者的补充议定书》第3条a款规定,偷运移徙者系指“为了直接或间接地牟取经济或其他物质利益而使某人非法进入并非该国国民或永久居民的缔约国”。尽管偷运得到了移徙者的同意,但可能使移徙者陷于危险或有辱人格的处境。偷运历来是一种跨国活动。相比之下,贩运虽不需要国际旅行,却涉及对受害人的欺骗或公然胁迫以及在目的地持续对其进行剥削。此外,贩运者从这种剥削中获得收益,而偷运者和移徙者之间的关系在移徙者到达目的地并交付相关费用后就终止了。最后,贩运侵犯了受害人的权利,偷运则没有。
《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旨在将贩运定为犯罪,确保起诉并惩治贩运者,向受害人提供保护和援助并同时保护其人权,以此打击和防止人口贩运。议定书缔约方承诺在打击贩运方面展开合作。各执法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开展一致行动,可以有效地发现贩运活动,并为打击这种恶性犯罪提高认识和筹集资金。尤为重要的是,根据《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24条的规定,在起诉贩运者时向证人提供保护。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编写的《建议的人权与贩运人口问题原则和准则》对涉及贩运的人权问题提供了指导。
由于贩运和偷运具有非法性质,没有对所涉人数的可靠估计。现有数据主要来源于警察报告或那些不能代表全球活动的小规模项目。移徙组织的受害人数据库共有9 000多个案件。大多数报告认为,贩运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大,多数受害人为妇女或儿童(即年龄不满18岁的男孩或女孩)。在150个国家中,每年与贩运有关的起诉数量居高不下,2003-2004年期间平均为7 300件(U.S.State Department,2005)。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保存了从各种来源获得的关于偷运人口的描述,包括大约4 500个案件,其中70个案件与女性受害人有关,32%涉及儿童。尽管这些资料不一定代表世界各地的贩运活动,但它们显示,若按严重程度排列,受害人主要来自亚洲、独联体国家和非洲。受害人通常从低收入国家流入中等收入国家,或者从任何这些国家流入高收入国家。 鉴于贩运以及组织贩运活动的网络具有复杂性,正在尝试采取若干政策性对策。反贩运措施若要取得实效,就应多管齐下,包括预防、调查、起诉和保护受害人等要件。就预防工作而言,向移徙者招聘公司颁发执照的国家的当局已开始进行突检,核查这些公司的做法。针对潜在受害人的宣传活动十分普遍。一些国家正在设法制止那些让未成年人陷于极易受到伤害的处境的活动,例如非正式收养儿童。在起诉贩运者方面,各国当局正在根据情报,采取先制性调查。正在不断扩大国际合作,发现并打击复杂的跨国贩运网络。一些国家政府给予受害人暂时或永久居留许可,给予他们反省期,以恢复健康、评估形势并决定是否愿意向调查和起诉罪犯工作提供合作。各国政府还经常在民间社会组织的协助下,向受害人的康复提供协助。
国际移徙与发展:人权、性别、融入社会和应享权利(3)
C. 融入社会
移徙的成功在于移徙者和东道国社会的相互适应。为了完成这一适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移徙者在目的地国居留时尽早促进他们融入社会,符合移徙者和东道国社会的最大利益。融入社会的基石是平等待遇和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融入社会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有能力用当地语言进行交流、准入劳工市场和就业、熟悉风俗习惯、接受东道国社会价值、有可能与直系亲属相伴或团聚和有可能入籍。如果移徙者有权享受社会服务以及他们作为工人的权利得到保护,就可普遍促进他们融入社会。政府可为协助移徙者融入社会提供特殊服务或方案。民间社会可协助促进融入社会、分发移徙者可享有的各项服务的资料、适当时提供这些服务、促进移徙者参与指导融入社会进程。
作为东道国的居民,移徙者有责任了解东道国社会的法律和价值,不仅有义务尊重他人的权利,而且也有义务特别是尊重他人的文化特性。而东道国社会必须尊重移徙者的文化多样性和权利。可通过利用移徙带来的社会和文化财富,促进相互了解。
对移徙者对东道国社会的社会和文化融入进行的分析表明,在容许移徙者按自己的速度适应社会的有利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他们做得最好(Papademetriou,2005年)。在此进程中,各级政府在促进和资助推动社会融入的灵活和创新战略时,必须承担责任,制定标准。政府不仅应当宣传包容、公平和平等,还应建立实施机制。
政府必须保护移徙者不受歧视、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打击,特别是采取有效措施,不让他们的人权受到侵犯,不让他们受到歧视。通过宣传战略影响公众对移徙者的看法也十分关键。宣传战略应阐述和解释现行移徙政策如何符合社会接纳和融入移徙者的需求和能力。管理多样化和促进不同文化间交流的各项战略必须成为任何移徙政策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政府不应让蛊惑民心的政客垄断有关移徙的舆论走向,不应危惧不容忍威胁。机会主义者往往利用民众对移徙的忧虑以寻求政治利益,任何国家都承担不起因这些人的不负责任的言行而使社会结构遭到瓦解的后果。移徙者对很多国家的繁荣一直并将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有责任打造相应的舆论。
国际移徙与发展:人权、性别、融入社会和应享权利(1)
A. 人权
国家享有决定什么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入境和居留的主权权力,但须遵守条约义务和习惯国际法产生的各项义务。此外,根据习惯国际法和协定国际法,国家有义务维护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多数国家都加入了确立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从而要求维护和尊重这些权利的国际条约。当然,国家完全可以选择给予移徙者比国际条约所列范围更广的一些权利。
国家确定的居留条件既包括移徙者获得的比公认的权利还要多的各项权利,也包括移徙者在本国以外的一个国家居住时必须履行的义务。一般来说,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籍人除了某些政治权利以外,享有与公民同样的权利。但是很少有国家在第一次准许移民入境时,就容许其长期定居。就多数国家而言,按临时类别入境的移徙者不享有与公民同等的权利。例如,临时移徙工人往往只限于做特定工作,或为特定雇主工作,不容许直系亲属陪伴或与其团聚。
将重点放在准予临时移徙者入境的国家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它们不愿意给予大批外籍人长期居住权,这就意味着为居留和工作设置条件,减少了移徙者的经济和社会融入机会,从而增加了由此造成的边缘化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而且这些条件的设置使移徙者容易受到虐待,可能违反国家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原籍国也面临相应的两难境地:如果移徙者不在另一国重新定居,结果反而可能更加有利,因为临时移徙者的家人仍留在原籍国,与定居海外者相比,他们更有可能向国内汇款,以及在回国时带回存款。此外,临时移徙者更有可能回国,无论是暂时还是永久,更有可能为原籍地的发展作出贡献。但是原籍国也知道,如果这些移徙者在目的地国享有定居保障,他们的日子会更好过。从移徙者来说,如果能够合法地在海外工作,总比偷偷摸摸的移徙和工作要好。
移徙的日益重要性使得国家不得不找到走出这些困境的可行办法。由于今后几年对于移徙劳工的结构性需求不会消退,可能仍有机会在一段时间内让某些移徙者从一种移徙类别转换到另一种类别,并让他们在此过程中获得进一步权利。对于定居国的永久移民来说,这一过程可能最终导致入籍。移徙者在成为公民后,便获得所有各种权利。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家,从一个类别过渡到下一个类别就等于提供了机会,可确保移徙者在融入的同时也进入了延长其居留期的进程。
容许为家庭团聚进行移徙的国家可促进家庭成员适应和融入东道国社会,特别是确保受扶养人的移徙者身份不一定要与作为担保人的移徙者身份捆绑在一起。限制移徙者或公民的外籍配偶加入劳工队伍,可能对其身份或融入产生不利影响。没有独立的移徙者身份或从事工作的可能性,特别是已婚移徙妇女会容易受到虐待。
有些做法增加了移徙者的易受伤害性,应当避免或宣布违法。某些国家的雇主扣押了移徙工人的护照和旅行证件,从而有效剥夺了他们按本身意愿自行旅行的自由。将移徙者与东道国社会隔离、防止他们象公民那样组织或加入工会,或者不向他们提供申诉冤情的可信机制,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更有可能受到剥削。在某些情况下,男女移徙工人都面临这种风险,但是从事某种职业,特别是作为帮佣工的女性移徙者,其权利更容易受到公然侵犯。
处于非正常情况下的移徙者尤其容易受到剥削,因为他们一般都不能或不会毫无顾虑地寻求当局保护。因此雇主更有可能利用这一点,付给他们的工资很低,或让他们长时间工作,有时是在危险的条件下。他们对公民来说也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结果是每个工人都是受损的一方:移徙者受损失是因为他们受到剥削,公民受损失是因为他们被有效地阻止从事移徙者从事的工作。虽然一般来说,政府并不宽恕这种做法,但是它们很难确保雇主遵守劳工法。对雇用处于非正常情况下移徙者的雇主实施严厉制裁是控制非正常移徙的一种常用办法,但是其有效性取决于是否严格执行,这并不容易做到。最后,不符合供需力量的法律和条例在控制劳工市场方面可能行而无效。如果对工人有正当需求,那么为他们的就业提供合法途径,确保他们的劳工权利得到保护,对各方都会产生最佳结果。
国际移徙与发展:人权、性别、融入社会和应享权利(4)
D. 养恤金福利和医疗福利的可携带性
一般来说,让老龄人携带养恤金比移徙者实现其他福利金的可携带性要容易。即使这样,据估计,绝大多数国际移徙者所面临的障碍是,由于他们在海外工作的时间有限,而不能携带养恤金,或丧失福利金。
多数发达国家的法律容许在海外支付养恤金,即使支付养恤金的国家与有关人员居住国之间没有一项特殊协定(Holzmann、Koettl和Chernetsky,2005年)。但是,除非受到双边协议的保护,在海外支付的养恤金福利可能受到削减。还有必要签订双边或多边协定,确保终其一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工作的人,不会因为没有达到他们所缴付的任何一个养恤金制度要求的最低缴付年限,而受到不当处罚。双边协定通过容许将所有缴付期合总计算,使移徙者能够从他们缴付的不同制度中获得养恤金福利,确保他们从其中每一个制度中获得公平的折合率。多数关于养恤金可携带性的双边协定容许移徙者直接从他们工作和缴付国家的社会保障机构获得福利金。这些协定并不设想在有关国家的社会保障机构之间转拨缴款。
在国际一级,1982年劳工组织《关于建立维护社会保障权利国际制度第157号公约》是唯一一项专门为了加强养恤金可携带性的国际文书,但是只得到菲律宾、西班牙和瑞典三个国家的批准。欧洲联盟《第1408/71号条例》载有广泛条款,确保在欧洲联盟内移动的欧洲联盟公民享有全面携带社会保障金的权利。2003年《第859/2003号条例》将《第1408/71号条例》的规定延伸到包括在欧洲联盟某个成员国居住五年以上的第三国国民,前提是他们不是难民。此外,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之间的欧洲-地中海协会协定,为这些国家在欧洲联盟工作的移徙者可携带社会保障福利金作出具有深远意义的规定。欧洲联盟成员国还签署了2500多项社会保障双边协定,多数是与其他欧洲国家签订的。其他地区没有关于社会保障可携带性的相等协定。
亚洲国家签订了121项社会保障协定。临时接受移徙工人的亚洲国家容许有限携带长期福利金,或像大韩民国那样在海外支付养恤金,或像马来西亚那样,当移徙者永远离境时提供一笔总付。在海合会成员国,移徙工人不得参加国家养恤金制度,但是也免除向这些制度缴款。因此,这些移徙者需要加入私人养恤金计划,或持续加入原籍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菲律宾移徙者在海外时可以向本国社会保障制度缴款,因此退休时可享有养恤金福利。
在退休后携带医疗福利方面障碍更大。一般规则是,移徙的养恤金领取人有权在支付养恤金福利的国家享有医疗福利。不能携带医疗福利往往阻碍了移徙的养恤金领取人永久返回原籍国。有些国家签订了双边协定,由雇主国偿付移徙退休者在原籍国产生的保健费用,前提是这些退休者必须有资格从雇主国领取养恤金。然而偿付的保健费往往不足以承担移徙者的自付费用。在另一些国家,是根据回国移徙者平均保健费用估计数,由雇主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向退休国作出偿付,从而使偿付的转拨更加公平。
对很多国家来说,医疗福利的携带因医疗福利和规范这些福利的法律不同而受到损害。医疗福利的不可携带性意味着,由于移徙者在年轻而较少利用医疗服务时向雇主国的公共卫生制度缴款,而在进入老年之后却依靠没有作出主要缴款的原籍国的公共卫生制度,使原籍国为这些回返的退休人员承受了不当的负担。
由于各国对退休后社会保障制度和保健应享权利有不同的规定,这些应享权利的可携带性可能多数仍需由双边协定来管理,当然它们可利用多方商定的标准。就养恤金的可携带性而言,关键因素是可以对各个缴款时期进行总和计算,以保护享有资格和确保公平的折合率。至于说保健福利,最佳做法是由支付养恤金福利的国家为退休人员偿付平均保健费用,确保这些退休人员能够充分加入定居国的保健制度。
国际移徙概览:2005年基本数据
2005年,国际移徙者人数为1.91亿,1.15亿在发达国家,7500万在发展中国家。1990年到2005年之间,作为总体,高收入国家的国际移徙者人数增长最多(4100万)。
2005年,全部移徙者中四分之三仅居住在28个国家。全世界每5个移徙者中就有一个在美国。
在41个国家,移徙者至少占人口的20%,其中31个国家居民不到100万。
女性移徙者几乎占全世界移徙者的一半,在发达国家则比男性移徙者多。
每10 个国际移徙者中有将近6个居住在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包括22个发展中国家,例如巴林、文莱、科威特、卡塔尔、大韩民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全世界1.91亿移徙者中大约三分之一是从发展中国家迁到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另外三分之一是从发展中国家迁到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南南”移徙者与“南北”移徙者大致一样多。
1990年代期间,经合组织国家年龄25岁以上国际移徙者增加人数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移徙者接近一半。2000 年,每10名居住在经合组织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移徙者中有6名来自发展中国家。
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移徙对目的国的影响
A. 移徙在全球的经济影响
移徙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展主导移徙,移徙反过来又影响发展,影响的方式有时并非显而易见。然而,由于大多数研究都着重于目的地国的情况,我们对国际移徙的全球影响力的了解S远不及对这种移徙在目的地国的影响力的了解。但我们知道,1870-1914年跨大西洋大规模移徙是第一个“移徙时代”西欧与美国工资水平趋同的最重要一个因素(Hatton and Willianson,2006)。此外,在同一时期,欧洲和非欧洲移徙潮流有不同分支,明显各异,结果助长了南北不平等(Lewis,1969;United Nations,2005a)。同样,当今世界的收入分配日益有利于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和高技能劳工,越来越不利于流动性低的要素,包括低技能劳工(Rodrik,1997)。换言之,更自由的劳工国际流动不仅有助于提高全球的收入水平,而且有助于更公平地分配收入。
最近,世界银行指出,国际移徙的惠益超过商品贸易自由化的惠益,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这一结论以世界经济总体平衡模式为依据。该模式模拟国际移徙增加对有关各方收入的影响,分析了两种假设情况:根据基线假设,2001 至2025 年期间国际移徙趋势为每一区域国际移徙者比例保持不变。而根据移徙假设,在2010 至2020 年期间有1 420 万新移徙者,包括450 万技术工人,从发展中国家来到高收入国家,移徙人数比2000 年国际移徙者人数增加8%。与基线设想的情况相比,在移徙设想的情况下全球收入增加0.6%。此外,发展中国家(包括其出国移民)的收入总额增加1.8%,高收入国家国民的收入增加0.4%。收入的增加既包括工资,也包括投资回报。新近移徙者得益最多。与基线假设情况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收入也平均增加0.9%。有损失的是较早的移徙者,由于很容易被新移徙潮所取代,他们的总体消费水平会下降6%。这些结果与关于移徙在经济方面对接纳移徙者的经济体的影响的研究是一致的。
B. 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根据经济理论,移徙会降低目的地国的工资水平或增加失业人数。然而,下文列出的证据显示,这些影响即使有,也十分微小,主要原因是如上文所述,就接受国绝大多数工人而言,移徙者并非取代他们,而是对他们的补充。新的移徙者只会同先到的移徙者竞争。移徙者与本国工人的互补性,有利于促进接受国的经济。
在目的地国,多数不同背景的研究都表明,国际移徙的增加对总体工资水平和失业影响甚微(Gaston and Nelson,2002)。但低技能移徙者的涌入影响较大的是降低已经在目的地国的低技能工人的工资(United Nations,1998;ILO,2004b)。不过在多数高收入国家,由于本国低技能工人所占比例很低,而且不断降低,因此低技能移徙者增加对降低平均工资的压力很小。在美国进行的研究表明,即使在移徙者比例很高的地区,移徙对工资和失业的影响也很小,但对于那些直接竞争移徙者从事的工作的人,即其他国际移徙者或具有类似教育水平和经验的本国人,这种影响可能较大(见Smith and Edmondson,1997;Borjas,2003)。专题小组研究证实了这些结论(World Bank,2006)。
在工资相对缺乏弹性的地方,例如在许多欧洲国家,移徙者的涌入并不会降低工资水平,但可能会增加失业人数,在低技能公民中特别如此(Angrist and Kugler,2002)。在法国,这一结果是关于工资的规章造成的(Dustmann and Glitz,2005)。然而,如果移徙者是受经济扩张吸引而来,就业就可能增加,至少不会减少。因此,在1984-1989 年和1990-1995年,若干欧洲国家失业和移徙入境人数的变动彼此并无关联(SOPEMI,1998)。移徙人数增加带来消费的增加,这反过来又提高对劳工的总体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改善本国人的经济状况。
在多数目的地国,移徙者的职业分布与非移徙者迥异,这也表明两者的互补性。此外,移徙者在劳工市场的活动有特定范围,而假如没有移徙者,这类活动即使存在,也不会具备如此的规模。只要这种情况存在,经济就会受益。因此,总体而言,移徙能增加就业人数。Linton 认为(2002 年),移徙者从事特定职业工作,而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些职业。移徙人口多的城市通常会有本来不存在或少见的货物和服务,例如外国饮食或托儿服务等等。因此,在高收入经济体,低技能移徙者往往是对低技能本国人的补充,而非同他们竞争(Castles and Kosack,1984)。
C. 国际移徙者融入目的地国劳工市场
对移徙者来说,加入劳工市场、获得体面的就业是融入当地社会的关键一步。如果移徙者失业率全面高于非移徙者,或如果移徙者更可能长期失业,那么在劳工市场就可能存在系统性的歧视(Zegers de Beijl,2000)。因此必须考虑移徙者融入劳工市场的趋势。
移徙工人失业时,准许他们临时入境的国家要求他们离境。在一些国家,移徙者只能为特定雇主从事特定工作,他们的入境和居留取决于有工可做。如果是这样,上述情况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国的移徙工人人数在经济兴旺时会上升,在经济萧条时会下降,因而每次遇到经济调整,移徙者便首当其冲。1997年东亚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大批移徙者回国,原籍国得应付突如其来的工人返国潮流。
在多数移徙者具有永久或长期居留许可的发达国家,移徙者所占劳工比例通常相当高(见表10)。在经合组织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一直在上升。1998 年至2003年,一些国家移徙人数增幅尤其大。按增幅排列如下:卢森堡、爱尔兰、西班牙、美国、葡萄牙和意大利。
1990年代,欧洲本国国民和外籍人士的就业均增加,特别在爱尔兰和西班牙,其劳工市场吸收了大批外籍工人(SOPEMI,2005)。然而,2000年开始经济萧条,多数发达国家外籍人就业增长放慢,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的外籍人就业减少。甚至在1990年代,年轻(20至24岁)和年纪较大(55岁以上)的外籍人士和各年龄组的外籍妇女在寻求就业时都继续面临障碍。但比利时、法国和荷兰在推动外籍妇女就业方面取得成绩。
在经合组织多数国家,外籍人士失业率和本国国民失业率持续悬殊,引起不安,政府于是对移徙者就业和居留时间规定条件,否则不愿接纳更多移徙者。2003年,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挪威和瑞典的外籍人士的失业率至少为本国国民的两倍。在较新的目的地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海外移民国和卢森堡,失业差距较小。在多数国家,外籍妇女失业率高于外籍男子(SOPEMI,2005)。
在欧洲国家外籍和本国男性工人失业率的差距主要是两者社会经济特点的差异所致,但也不能排除歧视为造成这种差距的一个因素。在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这三个国家,甚至除去其他因素的影响,与配偶一起居住的外籍男性工人的失业率仍偏高。外籍妇女融入社会的困难,似乎影响其就业机会。即使除去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外籍妇女与本国妇女失业率也仍有差距,对有子女的外籍妇女而言特别如此(SOPEMI,2005)。
各国政府认识到必须促进移徙者融入劳工市场,以加强社会凝聚力。为此必须通过适当立法和反歧视方案揭露和消除歧视行为。由于失业移徙者通常缺乏在不断变化的劳工市场取得成功所需的人力资本,他们能受益于培训,以更好地掌握当地语言,发展职业技能。在职见习培训、咨询、对创业活动的协助等也很有用。可能有必要开设特别方案,以满足移徙妇女、年轻和年纪较大的移徙者或包括土著人民在内的特定背景的移徙者的具体需要。
D. 移徙者的创业
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大城市已成为世界性都市,移徙者开设店铺,销售来自母国的“异国”特产。移徙创业家使现有货物和服务种类更加丰富,为一些城市街区增添了活力,从而防止,甚至扭转了这些街区的衰败。移徙创业家的技能在所在经济体往往已告缺乏,而且他们愿意长时间工作,利用其社会资本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
先进经济体服务业在扩大,顺应这一结构变更,移徙者的创业活动和能灵活因应万变的消费潮流的小规模生产也在增加(Kloosterman and Rath,2003)。移徙者的经营通常在开始时仅为满足本族裔人的需要,随后才扩大服务范围,拓宽市场。这种经营往往集中在特定族裔聚居区附近,为移徙者创造了就业,也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经商的机会。经营扩大后,往往雇用更多当地人。
促进移徙者创业的因素包括移徙者大家庭具有凝聚力,能提供免费或廉价劳动的子女或兄弟姐妹众多,同乡开办的轮流借贷会提供了集资机会,移徙社区内社会网络强劲有力,社区内能依赖以信为本、强制守信的关系等等(Light and Rosenstein,1995)。创业机会无疑使移徙社区增添了活力,为移徙创业家通过积累财富提高经济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渠道。移徙创业家销售其原籍国的土特产,往往导致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增加。
与本国人相比,移徙者更可能自营职业。在联合王国和美国,移徙者及其后代在自营职业者中所占比例偏高。除比利时和法国以外,在经合组织其他发达国家,1998至2003年期间移徙者中自营职业的人数上升,无论按绝对数还是按在自营职业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统计都是如此(SOPEMI,2005)。在一些国家,外籍妇女更有可能创办小企业。例如在法国,北非移徙妇女开店经营的越来越多。2000年,法国44%的小企业外籍业主是北非人,46%是欧洲人(Khachani,2004)。
在美国,自营职业的移徙者的收入往往高于工薪族,即使计及自营职业的高收入专业人士,也是如此(Bradley,2004)。移徙群体往往专门从事特定类型的创业活动(Portes,1995)。在美国,来自印度的移徙者在小旅店生意方面独占鳌头;韩国人专长于零售生意;中国人开餐馆。在法国,开店的法国人退休后,由北非人取而代之;在联合王国,南亚移徙者开糖果店和报摊;在荷兰,土耳其移徙者开面包店、杂货店等。
在德国,到1990年代末,51 000名德国籍土耳其企业家雇用了185 000人,其中20%是德国人。73%的德国籍土耳其企业家依靠德国企业供货。德国籍土耳其人创办的公司越来越多地投入在土耳其以外的国际商业活动。德国政府为考虑创办企业的移徙者提供财政帮助和咨询,推动创业活动。奥地利、葡萄牙和苏格兰也有类似的措施(Pécoud,2001)。
在南非,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移徙者开办了各种小企业。许多移徙妇女从事街头贸易和跨界贸易,这种活动使她们增强了经济能力。一项研究表明,一个移徙企业平均创造三个就业机会(Peberdy and Rogerson,2003)。
许多移徙企业家承接了本国人脱手的企业。Millman(1997年)指出,在美国,随着许多年纪较大的本国出生的农场主脱离农业,越来越多的农场归讲西语的拉美人和亚洲移徙者所有。
对移徙者创业情况的系统评估结果不一。有人认为,自营职业对于在正规劳工市场获得就业机会不多的移徙者可能是第二最佳选择。移徙者自营职业能否增加收入的问题争论很多(Borjas,1990;Bates,1997;Waldinger,1996;Kloosterman and Rath,2003)。评估结果的部分问题是一小撮自营职业者十分成功,换言之,虽然自营职业者平均收入不高,但潜力很大。对美国城市移民社区的分析显示,同具备类似特点的工薪职工相比,自营职业者工作时间较长,按小时计算的平均收入较低(Logan and Others,2003)。尽管如此,移徙者中自营职业人数持续增加表明,自营职业有其他优势。例如,自营职业能使不熟悉接受国语言和习俗的移徙者获得就业;自营职业是一种家庭战略,据以积累财富,为下一代经济地位的提升打下基础;自营职业也是打进主流经济的可能途径。现有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自营职业移徙者取得成功(Bradley,2004)。
各国政府认识到移徙者创业的潜在惠益,已经开始为有意创办新企业的移徙者提供一些帮助。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为提出可行的商业计划并保证有一定投资的外国企业家签发移民签证。为了推动移徙者创业,各国政府应排除规章方面阻碍移徙者自营职业的障碍,无论是全面性的障碍,还是特定行业的障碍,并确保正常状况下的移徙者与本国人一样有平等机会获得金融服务,而且财产权受到尊重。
E. 国际移徙与城市复兴
国际移徙在防止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减少、调整其住房市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本国人纷纷搬到市郊区,城市人口增长减慢,因而形成了称为“逆城市化”的趋势。但在1980年代,逆城市化趋势止步,原因之一正是在大城市中心定居的国际移徙者不断增加。2000年,移民被认为是改变美国城市面貌的两个最强劲的人口趋势之一(Florida,2004)。在主要城市,如美国的芝加哥、达拉斯、休斯顿、洛杉矶、迈阿密、纽约、圣地亚哥、旧金山和华盛顿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入境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主要原因就是流入的国际移徙者人数超过了流出的本国人人数。大多数这类城市都是“全球性城市”,是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公司总部或政府机关所在地(Frey,2004;Pumain,2004)。尽管这些趋势的全面影响尚待确定,但这些都市似乎受益于国际移徙者的流入以及对住房需求的增加(Grogan and Proscio,2000)。
例如在纽约,外国出生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28%上升到2000年的40%,与此同时,房产升值,破落的街区复苏,犯罪率大幅下降(Florida,2004;Millman,1997)。此外,一些移徙群体迁入以前的穷区定居,给这些街区带来繁荣。例如,在布鲁克林的西印度群岛人往往一家有多人工作,他们利用本族裔人经营的非正式信贷系统购置平价房产,从而推动房产升值(Crowder,1999)。
在欧洲城市,居者很难有其屋的问题以及一些移徙群体住在市郊隔离社区的趋势产生了负面后果。在一些城市,新到来的移徙者都想租平价房,导致价格上涨。例如在巴塞罗那,移徙者为同样的住房所付租金通常高于本国人,而且形成了地区上的隔离(Domingo i Vals,1996)。在马德里,波兰移徙者往往在较贫穷的街区定居,但鉴于60%的波兰移徙者具有中学以上学历,30%上过大学,他们的住房条件日后很可能得到改善(Aguilera Arilla and Others,1996)。
同根同源的移徙者往往在特定城市定居,因而出现了移徙者聚居区,使他们能够保持与同胞的文化和社会关系,可以形成足够的人数,有利于族裔企业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移徙者立业成功,并能投资住房,这些聚居区可能变得繁荣;如果移徙者迁往他处较好的住房,这些聚居区可能沉沦,或者也可能停留于隔离、贫穷的状态。关于产生上述每一种结果的因素,还有很多情况尚待了解,但创建为社区服务的移民企业以及可能拥有住房这两者似乎是有利于产生有益结果的要素。
联合国秘书长在国际移徙者日的致辞
2006年12月18日
移徙体现了个人克服逆境、改善生活的强烈意愿。过去几十年来,旅行和通信设施的改善使渴望并有能力迁移异地的人数增多。
这一流动的新时代为全世界各个社会带来了机遇和新的挑战。它也让人们注意到国际移徙与发展之间的强大联系。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移徙带来的潜在好处。去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徙者寄回家的汇款约达1 67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国际援助总额。移徙者还利用自身的技能和专门知识,转让技术、资本和机构知识。他们在各个文化、经济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条充满活力的人的纽带。
令人遗憾的是,移徙者的经历也有不那么乐观的一面。愈来愈多的移徙者遭到走私者和贩运者的剥削和虐待。另一些移徙者遭受到歧视、仇外心理或种族主义的打击。在某些情况下,移徙者被妖魔化成接纳国社会的负担,即便客观的评价表明情况正好相反。
在结束这种虐待方面,国际合作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强调指出了联合国会员国共同制定的一组核心优先事项,从确保移徙者的人权、防止剥削和人口走私,到增加国际移徙给发展带来的好处,以便在渊源不同、但在同一社会或国家内共处的社区之间建立和谐关系。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公约》中也载列了许多重要的保障措施。但多数国家尚未遵守这一条约。在此国际移徙者日,我敦促所有尚未签署和批准这一公约的会员国,签署和批准这一公约,并在所有情况下给予所有移徙者他们所需及应得的权利和保护。
今天,受到国际移徙影响的人数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让我们共同努力,确保这一全球性的趋势造福有关各方——原籍国、目的地国和移徙者本人。
联合国秘书长:移徙作为发展的手段(3)
C. 跨国社区及其给发展做出的潜在贡献
跨国社区在国际移徙中发挥关键作用。目的地国的家人、朋友和其他联系人常常启动和协助迁移过程,从而促进和保持了人口移徙(Massey and others,1993)。海外的亲属一般是移徙的资助来源,他们还发挥作用,帮助新到的移徙者找到就业。来自同一个籍贯的移徙者常常在目的地生活在一个联系密切的社区,这促进了自助机构和志愿机构的建立。本国国民的帮助对于移徙妇女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她们比男子更依赖于目的地的社会网络,获得需要的信息(Massey and others,1998)。
跨国社区一旦形成,也发挥作用,促进原籍国的发展。上文分析了同乡会的活动和集体汇款的使用情况。此外,如果海外移徙者成为企业家,也会促进原籍国特有产品的出口。外侨也常常是进出目的地国的交通运输和电信服务的主要使用者。比如,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和墨西哥籍移徙者分别占前往原籍国旅游人口的50%、30%和20%(Orozco,2006)。随着海外社区的成长,目的地国和原籍国之间的空中交通量一般也随之增加。
海外移民也能有助于推动在原籍国的投资。例如,印度软件产业就得益于在美国有良好工作的印度人,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降低了印度在贸易上面临的声誉障碍,带动了在印度的投资。中国也得益于海外的华裔企业家,他们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创造就业,扩大出口(Lucas,2005)。
跨国社区活动造成的影响不大相同,主要反映了原籍国经济的不同。比如,印度软件产业的扩展是国家政策和其他国内举措造就的,主要是由大量训练有素、先前就业不足的工程师和信息技术工人保持的。
移徙者可以促成技术转让。不过许多方面取决于原籍国经济状况。收入较高的国家,如爱尔兰、以色列和大韩民国,比不大富裕的国家更能利用这些转让。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它们一般缺少利用技术转让的条件。因此,虽然小国和低收入国家在海外的技术工人比例往往更高,但其经济运行情况却改善不大。
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实行正确的投资政策,促进跨国社区参与地方发展,使后者受益。然而,为投资创造有利的规范环境并非垂手可得。例如,印度的出国移徙者在本国投资时仍面临障碍,菲律宾政府推动海外菲律宾人投资的努力似乎也没有成效。
同海外公民,尤其是高技术公民建立联系,可以协助建立更加积极的知识网络。积极鼓励和支持国内外研究人员成立跨国协会,也会补充这方面的努力。不过,一些更为活跃的正式网络似乎来自私人倡议,而非政府支持的努力。还很难看清这些网络在提高原籍国生产率方面最终发挥多大效益(Wescott,2005)。
移民网(ym16.com)为您提供最全面最新的移民相关知识和政策,帮助您解决移民中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其中《国际移徙与发展:就国际移徙展开政府合作(3)》的内容由移民知识小编2022精选编辑整理而成,希望对您的移民有所帮助,欢迎您通过移民政策专题访问更多精彩移民内容。